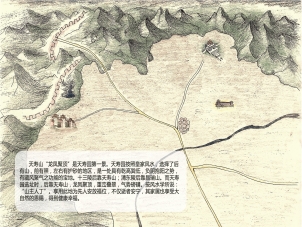昌平烈士陵园名单:镌刻在石碑上的英雄记忆
清晨的昌平烈士陵园,薄雾还未散去,松柏之间传来几声鸟鸣。沿着青石台阶缓步而上,两侧石栏刻着“浩气长存”四个大字,仿佛在向每一位来访者低声讲述那段烽火岁月。陵园始建于1956年,占地百亩,安葬着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以及新中国建设中英勇牺牲的688位烈士。管委会负责人介绍,名单最初由各村、各部队口述汇总,后经三次核查,才形成如今镌刻在纪念碑背面的完整名录。由于年代久远,部分烈士籍贯、生卒年份仍留空白,每年清明,志愿者都会携带拓印工具,为风化模糊的姓名重新上色,让失声的笔画再度清晰。
翻开《昌平革命烈士英名录》,纸张已泛黄,却能看见当年誊写员用毛笔写下的工整小楷:张兆瑞,1919年生,昌平县桃洼村人,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44年冬在执行护送电台任务时遭遇日军扫荡,为掩护战友突围壮烈牺牲,年仅25岁;李秀兰,女,1921年生,南口镇卫生员,1951年随志愿军入朝,在抢救伤员时遭遇轰炸,遗体未归,仅留一只绣着“平安”二字的针线包。这样的故事,名单上还有很多,短短几行字,就是一生。
烈士纪念碑后方的弧形墓墙按战役时期分区排列,每一格都嵌有黑色花岗岩,上面激光蚀刻姓名与生平。工作人员说,过去仅用水泥刻字,风霜雨雪容易剥蚀,2008年园区升级改造,特地从福建运来不易风化的“G654”石材,邀请非遗石刻匠人现场指导,只为让名字更久地留存。管理处设立“寻亲热线”后,已有47位烈士后人从河北、内蒙古、黑龙江等地赶来,他们在墙前点燃三炷香,用颤抖的手抚摸凹凸笔画,那一刻,名单不再只是文字,而是血脉的回响。
不少学校把入队、入团仪式搬到陵园,孩子们手捧菊花,在墓墙前依次喊出烈士姓名,声音稚嫩却坚定。老师会让学生随机挑选一个名字,回到课堂后查阅史料、撰写小传,并在下一场祭扫时朗读。六年来,累计完成人物小传两千余份,有学生在演讲比赛里说:“以前觉得烈士很远,当我把王永安叔叔的生平读给同学听,我突然明白,他就曾经和我一样,是昌平的孩子。”这样的教育让静态的名单产生温度,也让红色记忆真正走进下一代心里。

为了完善名单,档案局与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发起“补白行动”,一方面走访冀热察、晋察冀等老根据地,查阅发黄支前账本、伤残证、牺牲证明;另一方面利用新媒体发布“寻烈士后人”推文,附上陵园全景与墓墙局部特写,邀请网友辨认家中老人旧照片里的军装徽章。去年冬天,一位延庆老人看到推文后联系园区,说叔叔杨春和1947年牺牲在昌平整训期间,被就地安葬,但家人多年不知具体位置。经比对番号、年龄、牺牲时间,工作人员在墓墙角落找到几乎被苔藓覆盖的姓名,老人抚摸冰凉的石面,当场哽咽:“七十五年,终于找到您了。”

名单的补录也带来新课题:如何兼顾纪念与史实严谨?管委会制定“三重确认”原则:地方志记载、战友或亲属口述、实物旁证必须吻合其二,方可新增;对仅有孤证者,先设“待核实区”,供研究者继续考证。今年三月,园区新增11位烈士姓名,同时也有3个曾用名因与邻县烈士重叠,经比对后去除。有人觉得“删名”不敬,专家解释:“尊重历史才是最大的敬重,英名不能重复,也不能张冠李戴。”
夜色降临,墓区亮起柔和灯带,光束自下而上打在石墙,名字像星辰一样闪耀。守园老周每晚都要巡查三圈,他说自己听见风穿过松柏的声音,就像听见烈士在点名。“他们牺牲时大多二十出头,如果活到今天,也该是拄拐含饴的年纪。”老周把陵园当成家,三十年陪伴,让他对每一个名字都熟悉如邻里。清明、公祭、烈士纪念日,他总会提前擦拭花岗岩,确保雨水不留水渍,只为第二天家属来看时,姓名最亮、最清晰。
走出陵园,回望那面长长的石墙,名单静默,却像一条看不见的河流,连接过去与现在。它提醒人们,和平从来不是抽象名词,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用生命写下的注脚。下次再访昌平,不妨带上一枝白菊,在墙前轻声念出那些名字,让风把问候带给远方的英魂,也